建设独创性和共识性相统一的学术共同体

童世骏,出生于1958年9月,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兼任教育经济宏观政策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院长。
主要研究领域为认识论、实践哲学和社会理论,已出版学术著作十余种,其中包括《论规则》(上海,2015)、《中西对话中的现代性问题》(上海,2010年)、《批判与实践—论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北京,2007年;上海,2015)和Dialectics of Modernization: Habermas and the Chinese Discourse of Modernization (Sydney,2000)等;发表论文百余篇,其中包括“Reason and Li Xing: A Chinese Solution to Habermas’ Problem of Moral Motivation”(2013)、“Varieties of Universalism”(2009)和“重叠共识的重叠共识”(2008)等;出版译著近10种,其中包括《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德]哈贝马斯著,北京,2003,2011)等;主编丛书和专题论著若干种(部)。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第3期
此文发表在《探索与争鸣》杂志2016年第3期
“学术原创、学术评奖与学术共同体建设”圆桌笔谈
“学术评价”与“学术共同体”是两个相互定义的概念;没有学术共同体的学术评价,没有学术评价的学术共同体,两者都是徒有其名的。一方面,一位学者的学术论文的篇数和字数,乃至论文发表的刊物档次、论文发表后的被引次数,以及一个单位的科研项目数量、科研经费数量、获奖数量和进入人才计划的人数,等等,这些数据在个人申报高级职称、单位参加学科评估的时候,都相当重要。但对这些数据的统计工作,完全可以由秘书甚至工友来做,或者由计算机软件来做,而用不着劳驾同行专家,花费他们本来可以用来做更具有学术意义工作的时间。学术评价的核心,应该是同行专家或学术共同体成员对某学者之学术能力的判断、对某成果之学术贡献的判断、对某群体之学术分量的判断。另一方面,诸多学术同行坐在一起谈的如果只是获得多少科研经费、拿到多高级别领导批示,怎样发表更多外语论文,等等,虽然听起来都与学术有关,但却并没有对学术共同体来说具有“构成性意义”的要素,亦即对学术成果的质量评价。

学术评价至少运用两个方面的标准,一是学术成果的真理性,一是学术成果的相关性(或价值和意义)。这两点与学术共同体有内在关联。把学术共同体成员聚拢在一起的,是追求真理和解决问题这两个目标。以马克思主义和美国实用主义为代表的知识论中的“实践转向”之前,人们会把“追求真理”看作是认识过程的唯一目标;而“实践转向”之后,人们又会把“解决问题”看作是认识过程的唯一目标。其实这两个目标对于认识过程来说是同样重要、不可相互替代的。人类生活当然是一连串产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但问题的种类各有不同、解决问题的方式也各有不同;科学认识或学术研究之解决问题的特征,就在于通过获得具有真理性的知识来填补人类的知识匮乏,进而解决因为知识匮乏而造成的相关问题。这种问题可以是纯粹理论性的,但常常是具有不同程度的实践性的。自然科学领域有一句老生常谈,那就是常常是最初似乎只满足理论兴趣的重大科学发现或发明,后来被证明是具有重大实用价值的,如经典数学和现代数学之于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以及经典力学和量子力学之于现代技术和当代技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知识的社会性和功利性更加明显,因此学术成果的相关性或意义和价值在评价成果价值的时候会有更重分量。但成果之意义再大,也要建立在成果之为真理这一点的基础之上。更何况,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往往是研究者突破其特定社会地位和阶级归属的局限而追求真理的情况下获得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说,“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但马克思并没有把科学研究与阶级利益的关系绝对化;稍后他就写道,“但在这方面,进步仍然是无可怀疑的”。在举了几个例子,说明统治阶级的一些成员也承认“在奴隶制废除后,资本关系和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会提到日程上来”以后,马克思写道:“这并不是说明天就会出现奇迹。但这表明,甚至在统治阶级中间也已经透露出一种模糊的感觉: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马克思尤其赞扬“像英国工厂视察员、编写《公共卫生》报告的英国医生、调查女工童工受剥削的情况以及居住和营养条件等等的英国调查委员那样内行、公正、坚决的人们”,他们的研究报告为马克思提供了用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宝贵材料。

最能说明学术评价与学术共同体之间密切联系的,是知识进步所需要的那个看似矛盾的方面。学术成果既具有独创性,又具有共识性,只有在一个高水准的学术共同体当中,才可能实现统一。学术研究当然要具有独创性;“研究”之区别于“学习”,就在于虽然它们都着眼于解决问题,但前者所解决的应该是原则上尚未被别人解决了的问题,而学习至多是模仿或重温别人已经经历过的解决问题过程(所谓启发式教育)。学术研究成果到底是否具有真理性,既不能依靠“真理就是主观与客观的符合”这样的“真理定义”,也不能依靠“知识在实践中证明其真理性”这样的“真理标准”,因为用“标准”来考察是否符合真理之“定义”的整个“过程”本身如果不加以重点考虑的话,任何个人都可能声称自己的认识是经过“实践检验”而“符合现实”的。在一个努力以真理性知识来解决问题的一群人,也就是“学术共同体”当中,一个人说自己“掌握了解决问题的真理性知识”,是必须经受住学术共同体中其他人的质问,才能站得住脚的。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有关真理的哲学讨论当中,不能只有关于“真理之定义”的讨论和关于“真理之标准”的讨论,还必须加上有关“真理之认可”的讨论。因此,回答真理之认可问题的“真理的共识论”与回答真理之定义问题的“真理的符合论”,以及回答真理之标准问题的“真理的效用论”一样是不可或缺的。
随着自然科学研究越来越关注远离感性直观的微观世界问题,越来越关注需要多人力投入和多学科参与的复杂问题,真理的共识论和它所回答的真理之认可问题,更加值得我们重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谈论真理之为“符合”的含义更加复杂(如与化学理论的真理性相比,艺术理论的真理性用“符合”来定义,就要复杂得多),谈论真理之是否得到实践验证的含义更有争议(以毛泽东为例,他直到最后还坚信他的“继续革命”理论是经受了他所发动的“文化革命”的实践检验的),更需要走出独白的真理观,代之以对话的真理观,把认识主体理解为包括但超越诸多认识个体的学术共同体。关键在于,只有在这样的学术共同体当中,学术成果的“独创性”和“共识性”之间才能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它鼓励学术共同体成员的独创,但并不仅仅局限于诸多独创成果的“百花齐放”,也要求“百家争鸣”,让每一家都尽可能在其他家的质问面前捍卫自己,套用恩格斯的话,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证明自己的存在理由。如果一个学术共同体的成员都是真正把“追求解决问题的真理性知识”作为其最重要的成员资格的话,最后得到学术共同体成员之共识的,就应该是他们认为最具有独创性的学术成果,而不会是平庸伪劣之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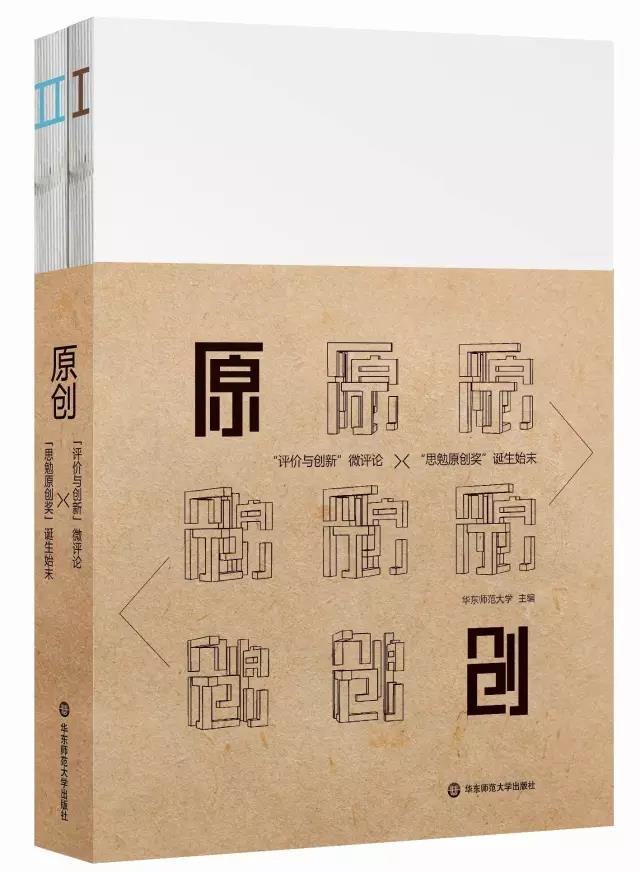
正因为学术评价与学术共同体之间的这种密切关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末尾的那句名言,同时包含了两个部分。前面一句是:“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紧接着的一句是:“而对于我从来就不让步的所谓舆论的偏见,我仍然遵守伟大的佛罗伦萨人的格言:走你的路,让人们去说罢!”在这个序言中,马克思花了许多笔墨来说明其观点尤其是方法的独创性——对作为一个学者的马克思来说,他的观点和方法越是独特,越是希望得到读者们理解和认可。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马克思说他对第二版所做的修改和补充,不少是根据其朋友(汉诺威的路·库格曼医生)的建议而做的。马克思深知这本书在工人阶级读者和资产阶级读者那里会有不同遭遇,指出“《资本论》在德国工人阶级广大范围内迅速得到理解,是对我的劳动的最好的报酬”,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不关心工人阶级以外的读者对《资本论》的反应。马克思嘲笑资产阶级学者起初企图用沉默置《资本论》于死地,然后,借口批评该书,开了一些药方“镇静资产阶级的意识”。马克思罗列了学术界对该书的各种各样评价,高度评价彼得堡出版的一个俄文译本的质量,并且大段引用一位作者的话,在他看来这位作者特别能理解和欣赏他的方法。这些都可以说明,即使是马克思这样一位阶级意识和斗争精神都很强的经济学家,也希望能找到一个他在其中可以验证其工作的真理性和重要性的学术共同体,一个把独创性和共识性统一起来的学术共同体。

扫描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